你好,欢迎来到中国女画家协会
中国女画家协会关于开展以“中国梦”
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的通知:
为认真贯彻中宣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以“中国梦”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通知精神,中国女画家协会决定在2014年-2015年开展以“中国梦”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活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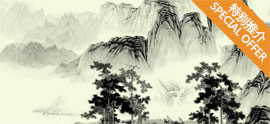

翟晶(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美术学博士)
“摄影如死亡”,罗兰·巴特在《明室》中如是说。摄影是存在的见证:不可化约的存在,一瓣掉落下来的时间碎片,与真实性或意义无关。那么绘画呢?绘画的本性是抽象,它再现的是感觉和记忆的合成之物,没人会认真相信绘画所说的,但却在绘画中寻求真实性和延续性,借用巴特的说法:“绘画如永恒”。
摄影与绘画的这种截然相反的属性,决定了它们之间总在相互角逐:摄影现身之时,正是绘画断裂、变形之际,摄影一面催迫着绘画不停地逃逸,一面却在无休无止地追逐绘画的踪影。图像世界就这样被分裂,但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合为一体:当代的绘画世界,有多少是以摄影图像为基础的,第二手的视觉经验早已取代了自然!
玛琳·杜马斯,一位在当代艺术世界成功胜出的画家。和很多人一样,她的艺术也分裂于摄影和绘画之间,又试图把两者调和起来。她近距离地使用照片,放大细节,强调即时性,使她的艺术带有某种“见证”的气质;同时,她又张扬绘画的表现能力,将笔法简约到极致,去除一切不相干的细节,尽力减少画面的歧义,以期到达永恒之岸。
玛琳·杜马斯的绘画带有政治性,主要关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,包括性别、种族、性取向、儿童、不同政见者等等。这个维度是显而易见的,也几乎构成了每一篇评论文字和展览前言的主题。杜马斯是荷兰裔南非女艺术家,出生于1953年,1976年移居荷兰,经历过种族隔离最严酷的时期,体验着作为南非人和白人的双重疏离,更分享了女性的尴尬与困惑,她是天然的“少数族”,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呈现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·巴巴所说的“无家性”。这样的特殊身份,固然使得她具有天生的政治敏感度,但更重要的是,她所成长的1980年代,正是各种政治话语主导文化和艺术世界之时,“身份”是关键词,女性主义、后殖民理论、同性恋研究等话语遍地开花,盛行于艺术创作、研究、批评、展览等领域。正是在这个年代,涌现出一批像杜马斯一样拥有“特殊身份”的艺术家:女性,有色人,同性恋,他们的“弱势群体”身份构成了一种天然的语境,支撑着其观点和视角的有效性,并迫使人们正视其存在。
毫无疑问,杜马斯属于这个时代的“政治艺术”,这是她作品中最透明、最常规的部分。无论是谁,只要对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学术语境稍有了解,都能穿越画面,直接读解到她的语义。这种特性使得杜马斯的绘画特别有利于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分析,也特别有利于维护西方人所十分看重的“政治正确性”,可能是因为这个,她自1990年代起,即在国际艺术界声名鹊起,并迅速奔入最贵的当代画家的行列。
然而我敢说,政治维度是杜马斯艺术中最平庸的部分,因为话语的(当下)有效性并不能确保作品的艺术价值,视觉艺术自有其规律,它必须直接作用于眼的感知,再穿透它,直达人的灵魂,两者缺一不可,如果它企图绕过前一个、或者回避后一个,就会导致话语泛滥、美学贫乏的奇怪现象,就会导致“问题”一统天下、“艺术”无处藏身的局面。杜马斯选择了一种主流的话语策略,并赖以成名,然而,如果她的艺术不能冲出策略的囹圄,如果她必须依赖问题的尖锐性,那么她最终只能从属于一个时代的艺术时尚,无法到达她所选择的媒介——绘画的永恒彼岸。
罗兰·巴特在《明室》里曾经为摄影区分了两种维度:“意趣”的维度和“刺点”的维度。
不止一次,我看到有人拿“刺点”作为一种理论工具,来分析杜马斯作品中一些突兀的细节,例如创作于2005年的《珍》中的乳头(图1)。但是仔细想想,巴特所讲的“刺点”,是一种无法通约的、纯粹个体的体验,它来源于某个不经意的细节和观看者之生命体验的巧遇,如同一道闪电,带来了伤害或狂喜。因此,“刺点”不可分析,不可分享,无法被用作普遍有效的分析工具。这正是巴特的观点中最可贵的部分:通过刺点,他试图将艺术还原为一种只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,不要分析它,让它安静,逃离话语嘈杂。因此他在谈到刺点时,总是采取第一人称:他在确认“个体”是欣赏视觉艺术的基本维度。在这一点上,巴特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和批评家,然而许多人却仍然向他认祖归宗,学习他、研究他、搬用他,尽管他们所想的完全和他相反,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
再来看《珍》,这幅画中的乳头的确够奇怪,让人无法忽视。然而奇怪的细节并不是“刺点”的要义,刺点存在于细节中,但那必须是不经意的细节,是脱离了作者本人的意图的细节,它对一个观众意味着全部,对另一个人却什么也不是,它是“偶合”,是徐志摩曾经浪漫地描述过的《偶然》,是一种纯粹的个体体验。这样的细节在摄影中比比皆是,而在绘画中,尤其表现性的绘画中,却十分罕见,因为精简的笔法正是要消除一切无关的细节,突出作者的意图。很显然,那个奇怪的乳头不是什么“刺点”,它是作者有意要你看、迫使你不得不看的东西。
在杜马斯的绘画中,我倒是轻易地认出了“意趣”。巴特的“意趣”属于理解的层面,诉诸你的文化修养,要求你以人道主义精神来认出作者的意图并对它(礼貌地)表示共鸣。“意趣”泛滥于各式各样的照片之中,尤其是新闻照片,或喜或悲,那些人物、场景、知识、隐喻,无一不在要求你去关注、去识别、去认可。杜马斯的政治维度无疑从属于这种“意趣”。她的作品很多都来源于新闻图片,也拥有新闻图片式的准确度,当她画黑人,你认出了南非的种族隔离之痛,当她画女人,你认出了当代女性在性别歧视下的种种痛苦,当她画尸体,你又认出了这个世界的暴力和不同政见者的遭遇……
然而不,等一等!你却发现自己无法淡忘这些“意趣”,而意趣本该是可以轻易地被淡忘的。杜马斯的画却折磨你,让你受伤害,让你寝食不安、乃至噩梦连连:你总是看见那些了无生气的尸体横在你的眼前;你被那些鬼魅似的夜精灵瞪视得辗转难寐;那些光着身体的女人倒是可以忽略,但她们为何面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黑洞?还有儿童,那些巨大的儿童……(图2-5)
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了巴特,他说过“意趣”包含着“冲击”。它和刺点不同,它显现被隐藏之物,却不刺伤人。再具体一点?它是“出其不意”,是稀有之物、或完美的抓拍、或快门的速度、或技术加工、或新的视角……迷路了。这些都不是杜马斯,杜马斯带来的是伤害,她深深割伤你的感情,这种伤害挥之不去,类似于战争创伤,是在集体中回荡、分享的创伤,每个人都逃不掉的创伤,绝对是直接诉诸情感,尖锐得无法被分析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杜马斯超越了她的话语策略,超越了“政治艺术”。
杜马斯常被称为“见证者”,是因为她的政治维度、她作品的即时有效性。见证是摄影的特质,见证,归根结底要诉诸“存在”,因此也是诉诸死亡。然而你看到了,分析摄影的理论工具,已经无法用来分析杜马斯,她不是个纯粹的见证者,不是那种让艺术充当“问题”之奴隶的人,一面急切地寻求摄影之死亡,另一面,她也热切地向往着绘画的永恒。
于是又有一个词“精神表现主义者”,依我看,这毋宁是指她的笔法。论笔法,她继承了表现主义传统,你可以在她笔下读到席勒和柯柯式卡。然而还不确切。你会看到,大多数时候,杜马斯没有“表现”,她只是在“显现”,她企图营造一种客观性,摄影的客观性,再在其中悄悄地潜伏下她的体验和看法。表现主义的画作往往是热烈的、丰富的,而杜马斯却常常冷清、空寂、了无生气,仿佛感情已经蒸发,只剩下无法磨灭的伤害。
疲倦,还有恐惧,是你可以跟杜马斯作品共享的感受。这疲倦如此彻底,让你脑袋空空;这恐惧如此尖锐,让你无法思考。这是绝对的疲倦和恐惧,它不诉诸理性,它直达感情。
《想象》系列(图6),创作于2002-2003年,它一定是杜马斯梦魇中出现的人物,每一幅画都有一个被捆住双手吊死的女人。在意趣的层面,你可以轻易的认出女性主义视角,然而它造成的恐惧如此之深,却让你无法回避。在《想象》之后,杜马斯画了《幸存者》(2004,图7),一个黑衣女人站在漆黑的门洞前,惨白的脸,震撼人心的一字眉,脖子上还有被吊过的痕迹,身体微卷着,模样真是吓人,然而你只感到解脱,一种虚脱的解脱。你分享了她的感受,是的,幸存是一种虚脱。
《作者之死》(2003, 图8),这个题目一定让你想起了米歇尔·福柯?如果你不曾被理论荼毒得太过分,如果你还不曾丧失你的感受性,你一定体验到了疲倦,属于死的疲倦。描绘死者,却没有任何恐怖,只有寂灭的平静。掩住了嘴的白色床单,深陷的眼窝,惨白的脸,以及惨白的画面,处处透露出的是疲倦。生之斗争已让人如此憔悴,死的一刻还摆脱不了它的样貌。死亡是什么?是归去的解脱,是未知的恐惧,是离别的不舍,是未竟之业的不甘?在这幅画面前,你却接触到了它最真实的面貌:疲倦,什么也不想说的疲倦。
现在,你已触及了真实,真实对绘画情有独钟。巴特曾经费尽心思地想在照片里触及真实,甚至将之等同于疯狂,在绘画中,你却淡然地遭遇了它。真实属于绘画,如同见证属于摄影,但,如果有人野心勃勃,企图同时占有二者呢?她注定被永远放逐于真实与见证之间,或者之外吗?她可以抓住它们,揉碎它们,造出一个新事物吗?
也许我应该恭维杜马斯,说她的确做到了。但她没有。她总在真实和见证之间摇摆,使她正如巴特所说的那样,接近于疯狂。她的作品是以摄影为基础的,她收集、使用各种图片,有时也自己拍,她执迷于这些二手经验,和许多人一样。破碎的图像世界,破碎的主体体验,这是后现代时期以来的主题。毕竟,我们的时代分裂于这些碎片之中,谁都能看到这一点,骗不了人。摄影的发展,尤其是家用数码相机的发展,只是推进了碎片化的进程。
有时候,杜马斯迷失于碎片之中,她画的那些有时效性的肖像,本·拉登或者戴妃,时尚女性,黑人,被笼子困住的女人,或者裸露性器官的人,语义十分清楚,经常被分析(批评家总是分析那些容易被读懂、被理论俘获的,不是吗?),却是她最不知所云的作品。这种时候,她真的妄想僭越摄影,去捕捉存在,充当见证者,最后只留下了意趣(图9)。但在她最好的作品中,她却找到了立足之地,她将破碎的经验统摄起来,将之造入一种永恒的有效性。这些作品,语义不清,却包含一切,例如1985年的《朱-迪·沃尔》(图10)。
这件作品来源于杜马斯拍的一幅照片。照片本身很传神,照片中的女人显得忧郁,眼神有些暗淡,充满了思考,手指点着嘴唇的动作似乎表明她在犹豫,额前的乱发又仿佛暗示着某种处境。“内敛的”,这是巴特在论眼神的章节里所提到的,他认为这是照片有可能达到的真实,一种混淆了存在和真实的、浸透了情感的“疯狂的真实”。转换到油画布上的这幅照片,以血色为主调,粗犷的线条勾勒出轮廓、点染出眼神,手指也是那样点着嘴唇,似乎陷入沉思。这件作品最常被提及的,正是这种血色,那是一种鲜红的、无法回避的血色,流溢于整个画面,似乎在暗示女性之生存状态的残酷与恐怖。这是作品的意趣的维度。然而与杜马斯的绝大多数作品相比,这幅肖像显得并不那么一目了然。首先是她的眼神:眼神是内敛的。然后是她的动作:动作是语义不清的。
当然,把它植入杜马斯作品的序列中,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之读解为一幅女性主义作品,这很可能就是作者的原意。但是且慢。这幅画的哪一点让它像一幅“女性主义”作品呢?女性形象吗?那个形象没有清楚的意义。血色吗?血色曾经同样流溢于埃米尔·诺尔德的作品,但他显然没有女性主义倾向。或者是点着嘴唇的动作?那个动作除了说明她在思考或犹豫,还能说明什么呢?作者的意见呢?作者的意见不代表谁,只代表她自己。
没有,没有清晰的语义。于是它悬浮在那里,悬浮在阐释落空的地方。这种虚空固执地一再凸现,无法被忽视,又不能被扩展。这种显现,就是真实,感受性的真实,诉诸灵魂的真实。
于是,让我们回到那个地方,回到开始的地方。摄影如死亡,绘画如永恒。谁能穿越见证与真实的迷雾,到达一个和谐的天堂?没有人会认真相信绘画所说的,但却在绘画中获得永远的安宁。一旦绘画开始烦躁,开始喋喋不休,开始迫使人们接受什么,它只留下了意趣。好在还有那些时候,比如在杜马斯的一些优秀作品里,绘画安静下来,它摆脱繁文缛节,目光变得锐利,穿透眼,直达心,将恐惧、虚脱、疲倦或意味深长的虚空直接投掷到你的怀里。除了接受,你别无选择。
所以人们爱杜马斯,一个从属于黑色美学的杜马斯,一个主流、但又非主流的杜马斯,爱她的一部分,而非全部。这种感觉太眩晕,令人无法命名,但是,这就对了。从眩晕开始,重启你的艺术旅程,差点被取缔的旅程。
